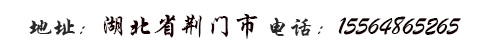新安文学微刊第3期
|
白癜风早期如何治疗 http://pf.39.net/bdfyy/ 本期导读 ■“安德利广场”好作品月赛开始啦 ■禾泉农庄小记/苏北(安徽合肥) ■一座村庄的气质/祖儿(安徽池州) ■鹞落坪纪行/乔浩(安徽怀宁) ■尚书里,采菊去/张辰保(安徽黄山) ■游横山小记/吴利民(安徽马鞍山) “安德利广场”好作品月赛相关事宜说明 1、作品要求:入选作品须为原创(原创首发优先),不得抄袭他人作品,一经发现,取消其参赛资格,文责自负。原创首发需在投稿时注明。 2、投稿方式:按照如下格式(标题+文章内容+作者笔名、真实姓名+手机号码+邮寄地址)投稿;同时将自己的简介和照片,与作品一并发过来。投稿邮箱是ljwxwx . 第三次走进太朴山下的元四村,我才慢慢品出这座村庄潜在的气质来。一 村庄的节奏总是和缓的,冬季村庄的节奏就更加缓慢了,因其缓慢,村庄才显得格外从容、安祥,这是脚步匆忙的城市永远也无法拥有的。 到达元四已是上午十点多钟,村庄还是一副刚睡醒的样子。初冬微寒,村头袅袅升起的炊烟,仿佛村庄打着呵欠的嘴里哈出的团团热气。鸡鸭比村庄醒得似乎要早一些,它们悠闲地踱到远远的稻田觅食,或到近旁的小河里游泳,一切都是懒洋洋的,随遇而安的样子,没有生活的慌张与急迫。 急什么呢?村庄的节奏本来就该是不急不忙的,庄稼人最懂得顺应自然的道理。 冬天的河流是和缓的,河水渐渐枯下去以后,河床一点点裸露出来,河流在冬天日复一日地消瘦下去,纤细得像是垂危之人游丝般的气息,随时会断流的样子。但从东河走到西河,再从西河走到东河,只见流水时强时弱,河床时宽时窄,河水却始终都没有断,它在一个又一个危险的当口化险为夷。俞河柔弱而又缓慢地流淌着,它从容地迂回,并不急于到达终点,因为不匆忙、不放肆,所以涵养出的河水也格外的清澈沉静,不着一尘。 村民的生活也是和缓的,老人在门口无所事事地晒太阳,女人在河边日复一日地洗衣裳,野菊花兀自在石缝里一年一度地开放。千百年来,河岸的石头被流水一点点磨平了棱角,浣衣的女人也一天天被流水带走了华年。她们在岁月里各自安祥地老去,相濡以沫,相看两不厌。 二 判断一座村庄的年龄,老屋与古祠是必不可少的参照,它们就像村庄额头上的皱纹,仿是仿不出来的,只能在悠长的岁月里慢慢地磨出来。元四随处可见的沧桑古桥、老屋与祠堂,便是它额头上深深浅浅的皱纹。 然而,也并非古老的就是有韵味的。有些古迹老则老矣,却老得松松垮垮,老得都托不住精气神了,哪里还有什么韵味可言。韵味是需要精神内涵的,它是有灵魂的。 曾经去过桐城的孔城老街,那里的老屋有强烈的年代感,一张张黑黑的门板就像老人饱经沧桑的脸。在一间昏暗的老屋里,我看见一个和老屋有着同样颜色的老太太,一手拿着发黄的线装书,一手拿着放大镜,就着天井洒下来的阳光,坐在厢房门口,神情专注地读书。我问她读的什么,她说:“《西厢记》”。这样的画面若放在别处,必定是突兀的,但放在这片老屋,我想说—符合孔城!孔城的气质是风雅的,多深的皱纹都挡不住这风雅点点滴滴地漫溢。 元四也是颇具古韵的,但元四的韵味明显有别于孔城。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古迹并非老屋,而是那些年代久远却保存完好的宗祠。 到底是兴旺过的,繁华过后,元四虽然已归于平淡,但历史遗存仍在,望族风范仍在。每年的腊月二十四,是章氏宗亲隆重祭祖的日子。一年一度,那对在仪式上熊熊燃烧了几百年的皇家火把,不知寄托了多少章氏族人对往昔荣耀的深情追忆。 元四的气质是肃穆凝重的,它不是小家小户过日子,而是大家族作派,对家族文明的敬畏与传承,使元四充满浓浓的宗庙气息。 三 一座村庄让人感觉亲切是简单的,使人感觉神秘就不简单了,它必须具备某种众所不知的要素,让人好奇,引人探究,令人神往。 从听章氏族人绘声绘色说傩的那一刻起,元四就激发了我无穷的想象。 有“戏剧活化石”之称的池州傩,本身就蕴含着太多神秘的元素。在我浅薄的认识里,傩就像一个身负特殊使命的人,它的身份本是尊贵的,原本有着高贵的血统,后来不知何因流落民间,从此普降祥瑞,为民驱邪祈福,为天下苍生求太平。 出于好奇,我曾经寻访过元四的“水口”,据说,那里是傩戏开场前,恭请神明降临的地方。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通往“水口”的崎岖小路上,我满脑子都是一种神秘的情境:天色渐昏,霜寒露重,一位神情肃穆的老者,怀揣虔诚之心,在人们的簇拥下,来到这个叫做“水口”的地方,顶礼膜拜,叩请神灵。然后,又率领众人回到祠堂,净手焚香,恭敬地请出阁楼上“日月箱”里珍藏的傩面具。 此时,戏台上的锣鼓已经准备停当,一场傩的大戏正在缓缓拉开帷幕…… 作者简介:祖儿,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陆续有百余篇作品发表于《新青年》、《思维与智慧》《扬子晚报》、《新安晚报》等省内外报刊杂志,著有散文集《修成一株安静的莲》。 一早从岳西县城出发,到达鹞落坪已是上午9时许。4月的鹞落坪还是有一些凉意的,只有我像是在有意与自己挑战似的,一件白衬衫,在众人中很是显眼。然而,由于我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却并没有感觉丝毫的凉。我已是急不可待的下车来。 这灵山秀水,我久蛰的思慕之情,它蠢蠢然似在蠕动。在这之前,的确有很多次来鹞落坪的机会,但终因繁杂的事务而耽搁至今。 这人世间总会是有的许多的遗憾,无论你身居何位。人的一生的成长都在经历遗憾,有时那些不完美,都会在努力和坚持下得到改变,人生若没有遗憾该多么无趣。我突然想到这些。 鹞落坪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与霍山县接壤,西北与湖北省英山县毗邻,地处大别山主峰区域,总面积平方公里。保护区内峰峦叠嶂,溪回谷幽。这里曾是当年红28军和皖西特委、皖鄂特委常驻地。 鹞落坪区内最高峰米,风景清幽,林木葱茏,气象万千,林海云海美丽壮观,是我早就神往的地方,现在我就在这儿。 来鹞落坪肯定是要去十里画廊大峡谷走走,十里画廊,是驴友们发自内的、由衷的对鹞落坪如景似画的命名。 沿着一条掩隐在林间的山路往前,它的终点是到达包家乡。这十里长廊两侧枝叶繁茂,山高林密,空气纯净,有一条溪流一路相伴,它那么娴静地于谷底流过,两旁连绵不断的山势,峰峦起伏,溪流潺潺,真是鸟语花香,美不胜收,宛若十里画廊,它的美用言语是难以表述的。 我等悠闲的走着,贪婪的呼吸着这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空气。 走了不多远,巧遇一位当地的山民,他在自家门前开垦出的几分地,种下的天麻正是收获的季节。他一边劳作,一边和我们交流着,谈收入,谈退耕还林,谈他自己现在的生活,显然,他的喜悦溢于言表。我因为职业的缘故,对他所讲的这些有更大的兴趣,更深的理解,还有我真切的体会。 保护区内是严禁开垦的,就是他家门前的这几分地也是绝对要经过批准,才可以种下这些天麻,任它自然生长。 陪同我们的H君,他是我的同行,又是一位摄影家,由他来客串导游是最好不过的事。 他身手敏捷,一会儿冲到谷底,一会儿跃往高处,抓拍着这鹞落坪自然保护区里独有的山中美景。我们一个上午就如此这样,感受着这鹞落坪百鸟齐鸣,山涧流水的妙趣。 回返途中,H君手指一处山峰给我看,山巅之上,一只鹞栩栩如生,那一双缓慢收敛的翅膀,会引起多少人的遐想。原来鹞落坪的名子由此而来,我记下了,它让我放慢了行走的速度。 只是鹞,这种物种已经灭绝了吗?至少现在已少见踪迹。大山依旧在,它沉默也呐喊着,而时间在飞逝。 那一阵阵或急或缓的松涛,它们在讲述什么呢?关于鹞的传说,已无从稽考。这神秘的大自然,还暗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也没人能说清楚。但是,我们必须要引起高度的警觉,这些年,自然环境日趋恶劣,给人类带来的教训已是太多了。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何等重要。 H君说,等秋天了,这山里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五彩缤纷,各种植物粉墨登场,真会让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你不妨再来,于月下饮酒,让月光晒晒,听枕边溪流…… 作者简介:乔浩,安徽凤阳人,现居安徽省怀宁县。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学院第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第一次知道尚书里,是很早的事了。那是从本地一幅摄影作品里见到的,作者是个女孩,名字好象叫文丽吧。照片是春耕时拍的。 青山环绕的村庄上,是弯弯曲曲,层层叠叠,成成块块的小梯田。梯田大部已被耕耘过,灌满了水。夕阳的余辉,从山头的那边掠过,洒进山沟那高低成片的田水里。那山田里的水,平静如镜,五彩斑澜,似被彩墨浸过的调色板。一位农夫,头戴草帽,正扶犁扬鞭田间。好一幅山居田园春耕图啊。尚书里,一定是桃源仙境,可能古代有位尚书,曾在这里,过着陶渊明一样的生活吧? 再以后,每到三口油菜花飘香的季节,总少不了尚书里的影子,那山坡层层梯田的油菜花,更是娇艳迷人,美不胜收。因此,对于那尚书里,心中,一直向往。向往那山坡,向往那水田,向往那油菜花。想象着,黄山脚下这小山村里,一定会藏着某种秘密。 初夏的黄山乡村很美,宛如情窦初开的少女,褪去了青涩,早已出落成熟,能落落大方地迎接夏天热烈的时光了。从夫子峰脚七弯八绕,就进了山里。车子在山中穿行,在绿丛中穿插。一条山径,不时隐没在曲折蜿蜒的山中。是哪儿?已不清楚了,云深雾浓处,我也不知身在何处了。 尚书里到了,车在一座小石桥前刚停稳,同行们就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溪口路边,到处是簇簇妖娆的小黄花。那盛开的黄花,金灿灿一片,点缀了山的美丽。路边和溪畔,它们争奇斗艳。草丛和山边,它们花枝招展。就连村口那小拱桥的石缝上,也朵朵鲜艳开花,生机勃勃绽放。 一条山径,就是一条黄澄澄的花径了,它顺溪而上通向村里。行走在花径里,听溪水潺潺,看山色青青,心情也同这山林里的空气一样,是清新的。花样的女人们在花中行走,象飞舞在花丛中的蜜蜂,让静谧的山间充满了笑语欢声。 小村不大,就着坞洼里的山势落座。村前村后,山峰绵延起伏,青翠欲滴,云蒸雾绕,从四面八方把这个小村庄拱围。淡墨轻岚乍起处,是轻风和溪流的笙歌。想不到,黄山脚下的深山里,还隐藏着这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一幢幢粉墙黛瓦,在万绿丛中忽隐忽现。一片片枫林竹海,在山腰荡漾摇摆。茶园成片成块,可能茶刚采过,时而露出地色,镶嵌在村子边的林带中。村后的山坡,就是那层层叠叠,一直排到山顶的梯田。 小路穿过村子,一直通到梯田中。毛竹丝扎成的篱笆,把房前屋后的瓜地菜畦,分隔成一个个花果的小世界。不管你在村中哪儿,都能见到那小黄菊的身影,它象个调皮捣蛋的小童孩,东躲一丛,西藏几枝。村中坡地虽不平旷,但屋舍俨然,绝不逊色于陶翁笔下那桃花源里的“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五月的尚书里,几乎每个山坡,每个溪旁,每条山道,都有野黄菊的身影。那山坡的梯田里,更是小黄花的世界。那一片片满满的金黄,象潮水一样涌到你的脚下,浩浩荡荡,一直平铺到山沟,从山腰延伸到山顶。它肆意的开,开得朴实而高洁,开得华美而灿烂。在百花争艳的季节里,它是青翠山村最热情的伴侣,它溢满了山间的每个角落,更熏醉了整个山坡。五月的尚书里,不再寂寥,有了黄野菊的装扮,而焕发出了高雅的生气。 置身于这样的花花世界,相信谁都会喜欢上,谁也不会拒绝的。爱花的女人们,都穿行赏玩于梯田的野菊丛中了。采花,赏花,与花共舞。或头戴一环,在花姿中招展。或手抱一丛,让艳压群芳。或拈花一笑,顾盼生情。或耳别一朵,绰约如仙子。 手机和相机盛行的时代,谁也不会忘记留存美丽。花海里的女人,俏丽婀娜,姿态天成,貌若天仙。在花丛中,她们扶芳闻嗅,淡扫娥眉。在梯田里,她们附蹲摆姿,轻点朱唇。在这样一个梦幻般的仙境里,呼吸着小村泥土芬芳,沐浴在青山绿色里,饱览着花丛间流淌的热情,大家忘情地沉醉着,叽叽喳喳的欢笑声,在山坳里不绝于耳,每人都回到了天真和烂漫的年华了。 采上一束鲜黄的野菊入手,细细的端详。黄色的花瓣,一瓣围着一瓣,有秩序地排列着,犹如一个金黄色的小太阳。娇小可爱的花蕊,紧紧地拥在一起,像一个害羞的少女。原来,它是如此的美丽和高雅。高傲的黄色,开在山野里。无意争春,却艳压群芳。 这野黄花,是一种五月的鲜黄,虽无莲的淡雅,但美得靓丽恬静,美得纤细瘦弱,美得让人爱怜。它比金盏花的茎高枝软,比波斯菊的枝繁叶茂。它不是野甘菊,也不是千里光,但是菊科植物无疑。在学校学得那点植物学知识,早已派不上用场了。请教学过中草药的爱人和高中同学,最终确认了。这山花中文学名叫蒲儿根,拉丁学名:Sinoseneciooldhamianus(Maxim.)B.Nord.,菊科蒲儿根属的,别称叫矮千里光,猫耳朵,肥猪苗,黄菊蓬。那就叫它黄野菊吧。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站在尚书里野菊飘香的花田边,雾中的黄山峰脉在眼前迷漫。在这里,确实有位如陶翁一样心境的尚书,在此山中的岁月里度过了一段时光,相信他也一定采摘过这黄野菊。 村里有位老人很热情,也很健谈。一路上,同我们介绍着尚书里,介绍着胡尚书,介绍对面叫茶叶红的山坞里,那白茶树的故事传说。他怀抱着的那个童孩,可能很少见过陌生的山外来客,从村中见到我们起,到山坡的花海边,头不是埋在爷爷的肩里,就是藏在爷爷的两腿间,还一直啼哭个不停。小山村平常很宁静,鲜有这么热闹过,可能是我们一大群人的到来,吓着了他。 仁者皆乐山。尚书里,相传是隋末工部尚书胡裕在此隐居而得名。据记载,碧山的胡珲是胡裕的玄孙,他整理修成了太平胡姓第一部家谱《胡氏家谱》,大诗人李白还亲临黄山,在碧山为他族谱作序,并写了《赠黄山胡公求白鹇》于他。 事世更迭,朝代变化,村中现已很难找到关于有关尚书的建筑古迹了,只有村民们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传说,再就是一块碑文遗留的文字,记录着曾经的故事。但山村里的野菊花是知时节的,它从古时一路开过来,越开越多,越开越旺,象山风一样,也象山民的日子一样,簇拥着你的脚步,追逐着一年又一年的花事。 五月里,到了黄山脚下的三口,切莫忘了,去尚书里采野菊哟! 作者简介:张辰保,安徽黄山人。系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摄影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著有作品集《湖畔的阳光》、《听风问泉集》。 甲午秋日,光普万物兴,风摇稻浪宽。乘青云,踏菊香,遂约数友,驱车同游涂县横山石门景区。横山又称“横望山”,因四望皆横而得名。其主峰“太阳宫”为市区最高点。 居史载,诗仙李白曾七次游此,下榻澄心寺,醉卧山中。并留诗云:“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也曾到秦人家。”此胜景,何如不引游者之心? 车泊山麓,徒步行。细风轻扑脸庞、耳畔,犹爱人之软语轻诉,亲之暖之,惬意竟不可言传。拾级而上,林荫道里,齐整青石,肩负游者之迹,无怨无悔,默默无言。周边野草轻浮迎接风之殷勤抚慰。偶遇数鸟,色异。或翔或栖,或啾或静。逸趣无穷,天然澄净秋画也,醉游者矣。山待开发,故游者无多,寥寥无几,三三两两,均不见,更添山之幽静。不禁轻吟:“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同感古之境哉! 夫登而高之,竟峰峦叠翠,林壑幽美,碧苔青青,溪流潺潺,如闻琴音在耳。清澈见底,卵石一览无遗,余观之形态迥异,忍俊不禁。或俏皮或沉稳,或躺或立,或似语似闹,天然浑成,惟妙惟肖。可爱之至,无法言辞。顿觉心旷神怡,赏心悦目。曲身掬捧清泉,濯尘,洁手,留倩影,遗欢笑。游者乐得其乐乎!又欲吟:“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立于石门下,桃树早已桃尽花残,寒枝寂寂,依稀婷婷玉立,楚楚动人也。一友动情云:“来年桃花更迷人。”所言即是也。有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途经澄心寺,见佛像,大大小小竟有百余多,慈眉善目,宁静祥和,余肃然起敬,未敢喧哗,恐惊扰佛祖。一友从商,见佛虔诚跪拜,许是祈福安康,许是求财源滚滚。问余拜否?余摇头笑而作答。余以为:佛于心,不图虚表也。心有自有,非形式方得。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与人为善,以诚为本,心怀慈悲,明灯高悬,佛自心中,福报自临。 余登高远眺,抚思茫茫,生之短促,俯仰之间,或悲或喜,将为陈迹,流于东江。于乐中肆意豪情,弃悲中放而歌之,岂不美哉!故今暂别车马喧,浅避红尘嚣,于一隅忘机。嗟乎!此乃桃源圣地也,叹作武陵人噫! 作者简介:吴利民,网名芳菲四月,安徽马鞍山人。有作品刊于《作家天地》《榴花诗刊》《怀诗通讯》,以及各大网站。 苏北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iweihuaa.com/zwhzl/6611.html
- 上一篇文章: 限时免费成都最美古风拍摄基地终于对外开
- 下一篇文章: 成都9月最新最全小区房价表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