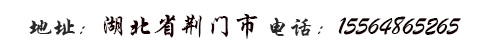丁立梅夏天的植物
|
凌霄 提笔写凌霄,突然捉不准凌霄花的样子,遂下楼,去看凌霄。 也无须跑多远,出了小区就有。小区后有小河,东西横亘,河边的桥栏上,就攀着一大丛凌霄。黄昏散步时,我会在那丛花边停一停。前几天,我在那里居然碰见一只小狗,它很认真地在嗅着一朵花。那画面真美好,让我一想起就感动,就要微笑。 河北岸是大面积的绿化带,里面有花廊,专门为凌霄花搭的。有半年的光景,那花廊是寂寥的,凌霄也是寂寥的,它赤裸着身子,像僵死的蟒蛇的尸体。然一俟花开,整个花廊就眉目飞扬起来,给人琴瑟齐鸣门庭若市的感觉。 这会儿,我先去看了桥边的凌霄花,又跑去花廊下。花廊下没有人,只有风,和阳光,和凌霄花。我在那花廊下走过来,再走过去,头顶上的凌霄花冲我吹口哨。我笑着仰头看它们,不自觉地也嘟起嘴,吹出一声口哨来。 凌霄花不单会吹口哨,还擅长拨弄琴弦,轻吐鹂音。——那花朵,太像一张会歌唱的嘴了,五瓣儿张开,微微向外卷着,橘色里,染着红。幽深的心房里,藏着琴弦。那贴壁而生的花蕊,真的很像几根琴弦,琴弦的顶端,还别具匠心地各系上一朵小花,浅淡的黄,粉嘟嘟的。 阳光照在花朵上,像给花朵镀了一层釉彩。它们看上去,很像一些精心打造的彩釉艺术品了。 凤仙花 我们长凤仙花,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为了染指甲。 凤仙花好长,种子掉哪里,哪里就能长出一大片,你追我赶地长,一心一意地长。 我家屋角后,每年都有成片成片的凤仙花冒出来。也无须特地播种,乡下的花,少有特地播种的。风一吹,你家的花,跑到我家来了。我家的花,跑去你家了。也有鸟来帮忙,把花种子衔得到处扔。有时,你在废弃的墙头,看见凤仙花,或是鸡冠花,或是一串红了。你也可能在哪个沟渠里,发现了凤仙花的影子。你不必惊讶,乡间的花,原是长了脚的。 我家凤仙花开的时候,真有些壮观了,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像落了一地的小粉蝶,吵嚷得厉害。我们不懂赏花惜花,只管把那些花啊叶子的,摘下来,捣碎,加了明矾,搁上几个时辰,染指甲的原料就算制成了。 天热,晚上屋子里闷,大人们也都要在外头纳凉。虫鸣喁喁,闲花摇落,星子闪亮,静下来的时光,总让人好脾气的。我妈和我奶奶,难得地坐到一起,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话搭话地说些碎语。我和我姐去挑了肥圆的黄豆叶子,让我奶奶给包红指甲。我妈兴致上来了,也会帮我们包。 捣碎的凤仙花,敷在我们的指甲上,上面盖上黄豆叶子,用棉线紧紧缠绕了。一夜过去,第二天,手指甲准变得红艳艳的。 刚包好的手指甲沉甸甸的,偏偏蚊子来叮,手却搔不了痒,急得双脚直跳,却舍不得弄脱缠好的指甲套。我奶奶或我妈,这时会笑着来帮忙。 露水打湿了头发,夜已渐深,却迟迟不肯进屋去睡。小小的心里,也有了贪,希望这样的静好清欢,能够地久天长。 丝瓜花 盛夏的乡下,最美的风景,莫过于满眼满眼的丝瓜花了。 那花是怎么开的?简直像一群活泼的孩子,在天地间撒野了,草垛上伏着,院墙上爬着,树上攀着。最让人惊艳的是,满屋顶的花笑逐颜开。是的,那是笑了,一朵一朵的小花,异常干净地笑着。仿佛就听见锣鼓喧天,厚重的丝绒帷幕缓缓拉开,它们就要来一场大型舞蹈了。 其实,单朵看丝瓜花,不美。但清纯、朴素的一张小脸,让你忍不住喜爱。是心底留存的洁净。而百朵千朵的丝瓜花一齐开放,就是壮观了。看着它们,心里不能不涌起一种震撼:微弱的生命,原也有这等的爆发力。 著名的写春天的诗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我猜想诗里的花,是桃花,或梨花。若是换成丝瓜花呢?定是千朵万朵压藤低了。那些丝瓜藤,实在美妙得很,细细的,沿着什么攀援而上。又是袅娜的,如风情万种的女子,有着纤弱的腰肢,一步一步,都藏了生动,藏了语言。牵牵绕绕,绕绕牵牵的,像蓄着一段暗生的情愫,理不清,说不尽。 遇到一蓬丝瓜。 不远处,野草们疯长,长得比人高,然丝瓜架上的丝瓜,却秩序井然,一朵一朵的小黄花,在绿藤上跳着舞,它们黄衣黄裙地穿着,再戴个黄头巾——它的蕊,多像团黄头巾啊,且是毛线织的那种。 看到它,我觉得亲切,亲切得如遇故人。我一得空闲,就跑过去看它。 记忆里,每年的夏天,它从不缺席。我奶奶在厨房后长它,一棵小小的丝瓜秧子,能牵出半屋顶的藤蔓来。开花时节,它给灰扑扑的厨房,很认真地簪上一朵一朵柔黄的花。它这么一装扮,平时不起眼的厨房,变得很好看了,叫人望过去多高兴啊。我们寻常的饭菜,也变得不一样了,似乎添了一些好滋味和好颜色在里头。 石竹 石竹花开了。这种花开得最用心不过了,每一朵,都像谁精心裁剪过似的,然后一针一线,缝制成小裙子。它的模样真的太像小裙子了,那些粉色的,镶了花边的,裙摆张开,迎风摇曳,是一堆小姑娘在舞蹈。我们小孩子也不懂珍惜,大把大把地采摘它,胡乱插满头。那些天,我们都是好看着的,都是一朵盛开的石竹花。 木槿 木槿,乡下人不当花,是当篱笆的,院边栽一排,任它在那里缠缠绕绕。 它在六月里开花,一开就是大半年光景,朝开暮落,白白紫紫,讨喜的小女孩般的,巧笑倩兮,一派天真。现在想想,那时的乡下小院,虽贫瘠着,然有木槿护着,又是多么奢侈华丽。 如今,城里多植木槿,路边,河畔,常能遇见。满目的深绿浅绿中,三五朵紫红,三五朵粉白,分外夺目,让遇见的心,会欢喜起来,哦,木槿呢! 乡下却少有它的踪迹了,喜欢木槿的老一辈人,已一个一个离去。乡下小姑娘来城里,不识路旁的木槿,我耐心地告诉她,这是木槿啊,以前乡下多着的。 这么说着,鼻子突然莫名地有些酸涩。时光变迁,多少的人非物也非,好在还有木槿在,年年盛放如许。 它又名“无穷花”。我喜欢这个名,生命无穷尽,坚韧美丽,生生不息。 顶喜欢到那河畔去,在夜晚。河里有船,载着一船灯火,突突突驶过。河对岸的树木茂密成岛屿。黑夜里望过去,真像岛屿。 我顺着水走,我把自己想象成是一条游鱼。两边的绿意堆砌着厚厚的静谧。垂柳或是七里香,又有些别的树木。我还认岀了木槿。它站在树丛里不说话。但我看到它的花朵了。黑暗里虽然看不真切,但我知道,它穿着一身淡紫的衣裳,站在那里,微微笑着。像个文静羞怯的小姑娘。 薄荷 不知它打哪儿来,最初的记忆里,就有它。 屋后吧,凤仙花开得呼啦啦呼啦啦,而它,姿态优雅地站立其中,恬淡地注视着,仿佛在看一群活泼的孩子,以一颗包容欣赏的心,由着它们热闹去。 最是奇怪大人们,咋就知道屋后有薄荷呢?他们是从来不看那些凤仙花的,但他们就是知道,哪里有凤仙花,哪里有薄荷。在他们眼里心里,每种植物的生长,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如同日升月落。他们吩咐一声:“去,到屋后掐几片薄荷叶子来。”那是因为孩子们身上生痱子了,奇痒无比。孩子们得令,“嗖”一声飞奔过去,胡乱掐上一把来,满指满掌,皆是薄荷香啊。他们拿它冲了热水,给孩子们泡澡。孩子们的身上,散发出薄荷经久的清凉。还真是神奇,只要洗上两次薄荷浴,孩子们身上的痱子就不痒了,不知不觉,消失了。 也有用薄荷泡茶喝的。不用多,沸水里丢下两片叶子足矣。我爸有个白瓷大茶缸,他每天早上外出干活,都泡上一大茶缸薄荷茶——凉着。暑热里归家,来不及脱了草帽,就奔向它,抱着它咕咚咕咚大灌一气,满足地长叹一声:“真过瘾啊。”秋深时节,薄荷也凋零,那个茶缸没有薄荷可泡了,我们拿了它去清洗,手指上缠绕的,竟都是薄荷的味道。长长久久。 栾树 夏天一场雨后,风变得没那么急躁了,湿润起来。去林荫道上走走,咦,平日走惯的路,跟往常不一样了,多了些香气。那香气,好闻得很,有些像炒熟的面粉,透着麦粒香。没费多大劲,我就找到源头了,吃一惊,原来,是栾树,它们开花了。且开且落,地上铺一层,被雨水浸泡着,体香就再也藏不住了,漫溢出来。 栾树的花,很细密,黄里印着浅浅的绿,一撮儿一撮儿的,藏在浓密的叶间。倘若不是有心去细看,还真就忽略掉了。谁知这平凡而细小的花里面,有着日后惊人的华丽呢!未来是个未知数,用平凡成就伟大,完全有着可能。对花如此,对人亦如此。 合欢 合欢始开,初见世面的样子。彼时,它尚未完全放开手脚,所以,开得含蓄,开得羞涩,试探着,把好颜色一点一点涂抹上去。不急,人家一点也不急。我却看呆了,多美的一树树花啊!尤其是在暮霭时分,那一丝一丝的绯红,尤显突出,温柔得能掐得出水来。 别的花是一瓣一瓣开的,合欢却是一丝一丝开的,慢慢开,如桑蚕吐丝一般。 我们以为还得等等哪,哪知稍稍一分神,它已织出一个小粉扑。——它的花,真像一个小粉扑,女孩子化妆,可拿它沾胭脂,扑在脸上。 有时看着,它又特像一个粉色的小绒球,可直接别在帽子上做装饰。 六七月,合欢花开得盛。 这个时候,我顶喜欢到那条合欢道上去走走。 “合欢道”——是我给它取的名。因道路两旁遍植合欢,树又高又密,花开时,青绿的叶上,浮着粉霞一般的花儿,远远就能望得见。 合欢花生得貌美,然体质纤弱,不堪风吹。风稍稍吹吹,花儿就掉了。我在树下捡那些花儿,能捡上满满一口袋。然后我一边走路,一边伸手在口袋里,愉快地碰碰它们。啊,手指上都是香的!那种香,有着小儿女的体香,温软的,甜蜜的。 合欢的叶子也可爱,白天,它们像花朵一样开放着,舒展着。到了夜晚,它们又像花朵一样闭合起来。那叶子闻上去,也是香的。 《红楼梦》里,有用合欢花泡的酒,宝玉喝着,黛玉喝着。这两个仙人儿喝着,我觉得极配。不知用它泡茶喝可好?我想尝试尝试。荷花 盛夏里,塘里的荷自然唱了主角,在层层叠起铺展的绿中间,荷一朵一朵,悄然盛开,如一阕阕小令。哪里能瞒得住风的耳朵?十里八里之外,风都能听得到它轻轻绽放的声音。风跑过去,收拢起一朵一朵的清香,撒得四下里飞溅。人闻到,一个愣神,啊,荷花开了。平淡的日子里,陡添一重欢喜,咦,看荷去吧。 满塘墨绿的荷的影,你映着我的,我映着你的。古人写它,“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又或是,“满塘素红碧,风起玉珠落”,哪里又能描尽它的丰姿?你想用千万个好来夸它,一时又无从说起。 荷在轻轻吐香,你甚至能听到它们的心跳。开尽的正在话别,相约着下一场花开再相见。含苞的“啪”一声怒放,花蕊间,盛满喜悦。 突然怀念起小时的乡下,几家人共用一个小池塘,平日的吃喝洗涮,全在里头。塘里面长菱角,也长荷。荷花开的时候,三五朵不等,撑着一张粉艳的大脸庞,站在池塘的一角,站在水的上面。它美,美得有些邪乎。在我们小孩的眼里,那是很奇怪的事。我们一度叫它“魔鬼花”,不敢去碰它。 荷叶我们却喜欢。我们摘下它来,当帽子,顶在头上。祖母还用荷叶做过粉蒸肉,真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午时,我走过小池塘,荷在池塘的一角,站着,红艳艳的。我静静看它,它也静静看我。天地间没有一点声响,鼓噪的蝉也停了鼓噪,小麻雀们也不闹了。我很希望它变成一个仙女,走上岸来。但到底没有。直到有大人走近,吓唬我,你这小丫头,一个人在这里犯什么傻呢,当心塘里的老鬼把你拖下去哦。我突然地害怕,转身就跑。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害怕什么呢?是害怕到河里去,变成一朵花吗?小小的心里,大约是害怕着发生变故的。你做你的花,我做我的小孩,这才是最好的。 满湖的肥绿之上,荷在。一朵。两朵。三四朵。红的。白的。红的似红粉佳人,巧笑盈盈。白的似白衣少年,清纯安静。荷开,不喧不闹,不挤不攘,那份安静,是骨子里的。它慢慢儿地,一瓣一瓣打开。它知道,好时光原是容不得打马飞奔的,须得一分一秒珍惜着,才不算辜负。 这是玄武湖,荷真多,多得快看不到湖水了。 我夜晚来看过一回。那时的天空太像汪着一片湖了,月亮是养在水里的一朵白荷,且是含苞欲放的那一朵,肌肤鲜嫩得近乎透明。我屏声静气,看月,看荷。风踩过一片月影花影,月和花皆静悄悄的,人的声音喁喁如萤火虫飞。我待到很晚,装满一口袋的月光与荷香。 清晨来看,是另一番景象。太阳醒得真早,才五点,它已蓄势待出。荷起得更早,它们梳洗一新,一个个神清气爽,像是要去赴什么盛大聚会。我的眼睛里装不下别的了,全是荷,它们踮着脚尖的样子,它们踩着舞步的样子,它们半遮半隐的样子,它们含情脉脉的样子,它们窃窃私语的样子——都是别的花卉无法模仿的。 我爱那含苞的。粉嘟嘟的,比婴儿的肌肤还嫩,真想咬它一口。但果真地让我去咬,我怕是又下不了口了——它实在是太柔嫩了! 我也爱那绽放好了的。那么大个脸盘子,明眸酷齿,光华熠熠,好比神仙妃子。它的花蕊金黄,像堆着一撮儿金子。它大方得很,一点儿不吝啬,托着这一撮儿“黄金”,要赠给有缘人。它的举止里,全是贵族气派。 莲蓬初结也好,如青发齐额的稚子。这个稚子趁人不备,偷溜出家门,踮着脚尖四下里张望,眼睛里跳动着无数颗好奇的小星星。 有男人蹲在一朵荷花跟前,蹲老半天了,他就那么看着那朵荷花,禅定一般。我在不远处看他,觉得有趣。 突然听到身后一声惊呼:快来快来,看这里的荷花! 随着声音落下,一男一女跑了来。 我笑起来,走开去。走一段路,忍不住回头看看,又笑。蓝天下,有荷在开着,有人在赏着,谁说这不是幸福事呢! 蒲 苦艾味苦,苦到骨头里,是愁眉苦脸的一个人哪,终年看不见它的笑。我们采一把苦艾,手上的苦味,搓洗很久,也去不掉,我们不爱。蒲却清清爽爽的,是喜眉喜眼的女儿家,又憨厚,又天真。它在水边端坐,罗裙青青,长发飘拂,那方水域,便都染着淡香。我们拿它绿绿的枝叶缠辫梢,每一丝头发,都变得好闻。 夏天,它抽出一枝一枝橙黄的穗,棍子一样的,我们叫它“蒲棍”。采了它,晚上点着了,可熏蚊虫。我们也举着它,当灯,去草丛里捉蟋蟀,捉蚂蚱。 小城新辟的观光带中,不知是谁的大手笔,竟辟出四五个浅塘,里面长的,全是蒲。阔别它多年,偶然遇见,我的惊喜不言而喻。我不时跑过去看它。它开花,嫩黄。它抽穗,橙黄的一枝枝,像棒槌一样的,昂立,长长的碧叶衬着,实在漂亮。它还有个别名,叫“水蜡烛”,真正是形象极了。它是替鱼照着光明,还是替莲和菱,还是心中本就生着一枝枝光明? 我每回去,都见有孩子在它边上玩耍。他们攀下一枝枝水蜡烛,在风中快乐地挥舞着。我为他们感到庆幸,有蒲熏着的童年,总有一缕清香在飘拂。 茉莉花 茉莉开花,香。 阳台上摆着一盆,一推开门,就闻见了。喜,奔过去看,是它开花了。 它的花朵小巧,初开时洇着红晕,有点害羞的意思。然后,开着开着,就大方起来,一身洁白,可以做女孩子的白裙子了。 花期却短,早晨开,午后我去看,它已整朵掉落。枝上别的花苞,却层出不穷地冒出来,这朵息了,那朵开,这样承接着,也能开上十天半个月的。 有一年,我买一盆茉莉,忙得没空照顾它,就把它搁在室外,任由它风吹日晒的,冬天也不曾顾惜它。等我想起来再去看它时,它已彻底枯萎。我心存内疚,没扔了长它的花盆,让它的遗骸在里面待着。 来年夏天,它枯死的根处,意外地冒出新绿,抽出新枝来。仅一枝,瘦得不堪系东风。然那新枝上,却很快结出了小花骨朵儿。不久,花真真切切开了,认真地素白着,认真地清香着,叫我惊喜了一个夏天,感动了一个夏天。 紫薇 紫薇花开,真是不得了的事,端的就是云锦落下来。不是一朵一朵地开,而是一树一树地开。哗啦哗啦,紫的,白的,红的,蓝的……颜料桶被打翻了,一径泼洒下来。每瓣花,都镶了蕾丝一般的,打着好看的褶子。瓣瓣亲密地挤在一起,朵朵亲密地挤在一起,于是你看到的,永远是大团大团的艳。惊艳——它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黄昏时的天空,像个贪玩颜料的小孩子,身上脸上,全都被颜料涂抹得花花绿绿的了,红的蓝的紫的粉的,哎,幼稚天真得不像话了。 却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天空,真是好看啊,率性、明丽,有着大把的热情。 紫薇花不声不响已占了半壁江山了。我一出小区的门,就被它们吓了一跳,这才几天没留意啊,路两旁,已全被它们给占领了,衣袂飘飘,浩浩荡荡。 “盛夏绿遮眼,此花满堂红”,它的出现,似乎专门为安慰盛夏而来。 伸手搔搔它光滑的枝干,看它是不是真的怕痒——这是每年遇到紫薇花时,我必玩上几回的事。可能是它头上缀着的花太多了,太沉了,它并未因我的抚摸而“彻顶动摇”。然想起它的别名——“痒痒树”,我还是忍不住一乐。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选自丁立梅作品 《写作原来好有趣:美丽的四季·夏卷》作家出版社出版购买链接往期精彩回顾 ▼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iweihuaa.com/zwhzp/8178.html
- 上一篇文章: 之一与你生日对应的花及花语
- 下一篇文章: 中旅自组团middot黄山高铁纯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