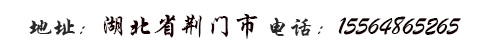褶子文摘李商隐,把存在变成美学的诗人
|
本期褶子文摘推送的是义山诗歌的爱好者吴蓝的作品。“存在”是贯通诗哲的人类永恒命题,李商隐的“存在”,以一种弥漫无际的孤独与虚无彰显着对于生命与世界的体认,诗人在这独特的体认中挣扎徘徊,感悟生活并重建自我。义山的诗歌,就是他这一心灵历险的印迹,通过把握现实里广阔的真实图景,用押韵的诗句把它敞露给灵魂世界,他持续不断地猜解着存在的意义之谜,最终这孤独上升为其独特的存在美学。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虚无的关切和把握,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义山诗深曲的思致,构成令人神迷的艺术秘境,令人每每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义山诗凄迷忧伤的情调,总是令人为之心动又深感无可奈何。义山似乎总在追求,也总在失落,总是失落,却又不懈追求,在这循环往复间,犹如舞蝶流莺辗转一春的悠邈悲欢,怅惘如梦;又如西绪福斯般透示着人类的悲情命运,以及在悲情前不屈的“存在”光芒。喜欢义山的读者很多,而要做义山的解人,我们不仅要读懂他的孤独与虚无,还要读懂孤独与虚无之后,犹如西绪福斯般的“存在”光芒;义山诗的美,不仅仅只是因为其金碧幽渺的词汇与意境,还是因为它蕴含着人类共通的心灵密码,图写着人类共通的精神景深,更是因为它说出了人类“存在”的奥秘。是“存在”通过诗歌构筑审美,或者说,是诗歌把“存在”变成审美,一切诗人或诗篇,其极致处,即为哲。潜入存在的诗人 诗、哲皆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使我理解到义山诗与“存在”的关系,是因为在我们当下的精神处境与生活状态下,义山诗是如此熨贴地就走进了我们的心灵世界,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的疏离。我们读李商隐,收藏那诗中的月明珠泪,正是寻求与构筑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提出的那个心灵故乡。本雅明在“巴黎研究”中继“震惊”之后提出了“内在世界”或“室内”的概念。似乎对于敏感的诗人来说,人群是一个更高的自我,由于面对众生的宽怀和紧张,诗人饱含着冲破个体的局限认识,将“人群”化为可以不断进入、走出的自我概念。在这样的自我中,作为个体的诗人成为不再孤立的存在,,那种超越认知罅隙的包容成为一种消弭孤独的存在。但是,这种以孤独为不孤独的越境似乎反倒印证了诗人更为深沉的孤独.由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和控制,人为了保持住一点点自我的经验内容,不得不日益从“公共”场所缩回到室内,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在这个居室里,一花一木,装饰收藏无不是这种“内在”愿望的表达。人的灵魂只有在这片由自己布置起来、带着手的印记、充满了气息的回味的空间才能得到宁静,并保持住一个自我的形象。孤独的现代人读几首李商隐的诗,用他的诗构筑每一个内在世界。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针对有些人指责存在主义对于虚无的描绘打击了人的积极性而言作出回应,指出存在主义在对人的更深切关怀中,主张发挥的是人面对虚无时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是更具有人道主义的哲学。同样,李商隐看似惆怅百转,婉约朦胧的诗的背后却是对人生的更真切的体悟,对人的存在的更深入的探寻。存在是贯通诗、哲的关于人的永恒命题,本文试图以“存在”为密码,尝试解开义山诗的存在美学难题。? 潜入存在的诗人存在主义把个人存在看作一切存在的出发点,认为人的真正的存在可还原为先于主客体区分的个人的纯粹的意识活动,由此可展现出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不同于物的存在,他是积极能动的超越的存在,即不断谋划选择和创造,这也就是人的自由。人的真正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人就是在自由的创造活动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和本质。人的本质的存在不能用传统的理性方法去认知,只能通过揭示孤寂、畏惧、烦恼、死亡等非理性的经验去领会。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在”是最普遍的范畴,其他各范畴都可从“在”中得到推演或定义,而“在”本身却不可定义。人因有领悟自身之“在”的能力而成为显现万物的澄明之所。与亚斯贝斯、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相比,海德格尔独特之处在于他的“以诗悟哲”方式。他说“诗人是在世界的黑夜更深地潜入存在的命运的人,是一个更大的冒险者。他用自己的冒险探入存在的深渊,并用歌声把它敞露在灵魂世界的言谈之中。”诗人李商隐显现了对海德格尔这一论述的有力支撑。对于强调个人化主观体验的诗人李商隐来说、他的存在是对于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无论生活的境遇怎样,利用成形的自身体验,把握广阔的真实图景,持续不断地猜解着存在的意义之谜,而这一“在”在内验化的过程,沉潜、发酵,最终变为审美对象。他夜宿豆馆时敏锐地发现了隐藏在“芦叶梢梢”深处的夏景;在途经大散关遇雪时,忆念到亡妻曾为他缝制寒衣的往事。他对笼罩在斜阳暗影里和暮蝉声中的杨柳很感兴趣,而披拂着层层轻埃般暮雨的长安崇让宅中的紫薇花,也曾引起他一往深情的无限感慨。他的不少诗歌在某些舍本逐末的评论家眼中,好像都是“缠绵宕往”“一往情深”之作,好像都只是为了追求“蓬山”而向往“蓬山”,寄意“青鸟”而期盼“青鸟”。他们却忽略了诗人矢志不渝的高洁信念,忘记了这对卓越崇高理想的追求正是他对存在意义的探寻。十几岁就写出脍炙人口的《才论》《圣论》,追寻一个至高的完美理想的李商隐,感受敏锐,感情深挚,富于想象而才世无双。作为一个激切主张“安危须共主君忧”的诗人,李商隐原本具有“欲回天地”的中兴壮志,只因“凤巢西隔”,得不到朝廷重用,无从施展他的抱负和才略。身逢宦官专权、藩镇林立的动乱中唐,又深陷党争不得脱身,李商隐的生存何其艰难,引发他“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遣佳期更后期”(《一片》)的慨叹。深感于社会白云苍狗之变换,却从来不会过分习惯于这个世界。“。终其一生,李商隐像个孩子一样敏感,绝不会苟且于这个世界,而执着于真实的非虚幻的世界。所以,他要去寻那娇魂,要去取那桂宫留影,去忆那画舸蟾蜍。追寻,是李商隐诗中不坠的主题。他用追寻证明他是积极能动的超越的存在,他不断地选择和创造,在自由的创造活动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和本质,这本质即为真正的存在。“沉博绝丽”的美学 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认为人生是痛苦的存在,摆脱痛苦的方式就是进入理念的世界。理念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中间环节,把本质与现象连接了起来,把认识从意志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这就是审美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审美主体摆脱意志的束缚成为纯主体,注意力不再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iweihuaa.com/zwhzp/9926.html
- 上一篇文章: 艺术惠民德艺双馨入兰亭于恩东惠民展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