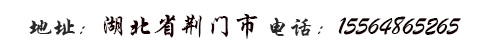花式冥想丨紫薇花对紫薇郎寄感
|
每年好象是从六月份开始,紫薇便开遍了开封的大街小巷。叫紫薇,但颜色不只有紫色,也经常见到粉色的,白色的。 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开得沉甸甸的,“千朵万朵压枝低”。汪曾祺说它开得“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照这情形看,《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倒比夏紫薇更配叫“紫薇”这个名字。紫薇,也叫满堂红、痒痒树,开封人习惯称百日红。根据《广群芳谱》里面的《紫薇》部记载:“唐时省中多植此花,取其耐久且烂漫可爱也。”省中是禁中的意思,紫微是古代天文学的三垣之一,也用来代称帝王的宫殿,也许这就是紫薇花名字的来由(微通薇)。祝穆的《贺新郎》就这样认为:“此木生林野。自唐家、丝纶置阁,托根其下。长伴词臣挥帝制,因号紫微堪诧。”紫薇夏至时节已然花繁,花期很长,古人称它“四五月始花,开谢接续,可至八九月”,故而又名“百日红”,这有可能是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曰:“似痴如醉弱还佳,露压风欺分外斜。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没有考究过。紫薇花曾见证了另一个诗人白居易的人生。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年),在地方任职多年的白居易奉召回京,累迁中书舍人,任职“紫微省”,即原来的中书省。唐代开元元年,把职在撰拟诏旨的中书省改称“紫微省”,因“紫微原为帝星,以其政事之所从出,故中书省亦谓之紫微,而舍人为紫微郎。”《新唐书·百官志二》:“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中书省改作紫微省,字面上就可以体味到在其中任职者拟诏出令,接近帝王的荣贵。所以,紫薇花还有权力仕途的象征意义义,世称“官样花”。中书舍人因为要随时根据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晚上是要在宫里值班的。一天傍晚,在值班的时候,面对着满庭盛开的紫薇花,白居易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就是被经常提到的“紫薇花对紫薇郎”。《韵语阳秋》中说:白乐天作中书舍人,入直西门,对紫薇花有咏曰:“绘编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黄昏中独坐几案,面前是成堆的公文,此情此景,庭院中的紫薇花愈是开得热闹,恐怕愈是有“蝉噪林愈静”的效果,更加助长寂寞来袭,所以诗中有一些类似于“寂寞宫花红”般的惆怅。但诗里诗外,也还透出些许自矜。毕竟,在这样一个位置,接近帝王,近水楼台,众人眼里前途无量。但是,前途无量只是一种可能,不是必然。白居易中年被贬为江州司马,浔阳江畔,再度看到紫薇树。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想起曾经的春风得意,一声叹息,再度写就一首《紫薇花》:“紫薇花对紫薇翁,名目虽同貌不同。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浔阳官舍双高树,兴善僧庭一大丛。何似苏州安置处,花堂栏下月明中。”因“紫薇花”和“紫薇郎”在字面上的相似,放在一起,多少有点“傻傻分不清楚”的感觉。导致每次见到这句诗,总是引起我关于哲学,禅学包括美学中都会涉及到的在“观者”与“被观者”的关系上有一个叫“物化”的概念的联想。物化这个词最早来自于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典故。《庄子·齐物论》中说:“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在这里用寓言来形象地说明他的“物化”意境,即一种泯除事物差别、彼我同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则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庄子哲学中关于如何看待事物的一个观点,即为“照之于天”,就是超越任何有局限性的观点,直达事物的本然。这种观点认为,事物的名称都是人给它起的,每种事物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庄子称之为“道”),从“道”的观点看,万物都是相通为一的。万物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有它存在的根据,没有什么东西是毫无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存在。所以,拿人(我)和物(非我)来说,从“道”的观点看,是没有区别的,是相通为一的。因而,庄周与蝴蝶也是相通为一的。同理,“紫薇花”和“紫薇郎”不仅字面相似,实质上也是相通为一的。道家这种“物化”或者叫“天人合一”思想的阐述,其实也体现在禅学的“梵我合一”(或叫“梵我一如”、“梵我不二”)上。在本来的印度思想中,梵即代表天、自然和普遍的原理、真理,是世界的本源,生命的根本,所有事物产生的原因。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中的那些隐居森林的修行者也被称之为修梵者。修梵有成的修行者可以被称为“梵行”很高的牟尼(智者、仙人的意思)。道家修炼很久的人,也都广被称颂,誉之为“道行”很高。得道者最高的层次被庄子称之为“天人合一”,与“梵我合一”类同。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哲学相接触,导致“禅宗”的兴起,在思想上更是与道家有某些相似之处。禅师的修行,要经过从迷到悟的过程,要把肉体的性情放下,进入禅定的境界。而在此后,他还要离开禅定的境界,重返世俗社会。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及到的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这第三种境界,我的理解也就是说既然从“梵”的观点看事物,万物都是相通为一的,又何必拗于它叫“山”还是叫“水”。这已经都不是个事儿了。据《传灯录》记载,有一个禅僧进入庙里,向佛像身上吐痰,庙里人批评他,他说:“请告我,何处无菩萨?”,好像也有“梵我合一”、万物相通的意味。同样的观点,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在禅语常说的“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着衣,未曾挂着一缕丝”中,也就是说人得悟了以后,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滞着的意思。所以,从“梵”的观点来看,“紫薇郎”还是“紫薇郎”,“紫薇花”还是“紫薇花”,反正只是个名字而已,就生命的根本、事物产生的原因而言,他们俩是一回事。在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发展史上,在“天人合一”观念的笼罩下,“物化”还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创造现象,所昭示的是文艺创造主客体浑一的忘我的精神境界。我们一般都是在“看”世界,高楼大厦,茅檐低小,都是我们眼中所观之物之景,我们和物都是观者与被观者的关系。这样一来,紫薇郎自是紫薇郎,紫薇花自是紫薇花,虽日与花对,终然邈千里。而“物化”要解决的是超越“物的世界”,进入一种生命的悟境,人融到物中,从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这时的“紫薇花”不是外在的“物”,而是与“紫薇郎”共同组成一个有意味的世界,彼我同化,哪里有观紫薇花的紫薇郎,哪里有紫薇郎观的紫薇花。我为世界所有,世界也为我所有。这种忘我是一种心理的超越。 《世说新语·言语》云:“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所谓会心,即物我关系消除,人与世界融为一体,人在自我创造的世界里得到心灵的安顿。苏东坡作品中时常可以看到对此的感悟,《记承天寺夜游》中写道:“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为什么时时有月,处处有竹柏影,而我们常常感受不到“此中有真意”。盖因在这个物欲的世界里,我们习惯于把世界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把自己作为一个掌控者,泯灭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灵觉。在《与子明兄一首》中说到:“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所谓“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已经与世界一无所隔,浑然与万物同体。在这种情形下,已经不是“我”看到了什么,而是“我”与世界共同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评文与可画竹时,他这样写道:“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丧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竹就是我,我就是竹,我与竹处于混化的状态,超越了爱竹的概念,而是直接的生命感知。在上述事例中,物化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引导下实现了审美创造的移情,主体和物象是合一的,在主体情思的笼罩下,物象充满了生动的艺术情趣,具有了真正的审美意义。以上我的这些胡思乱想,想来和当时的“紫薇郎”并没有任何关系。此时的白居易,心中充斥的还是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饱含着对社会的责任感,成天想的还都是入仕和有为。虽然字“乐天”,也只不过是内心痛苦不平的自我调节。直到中年以后,传统老庄道家思想和当时正蔚然成风的佛家思想,才逐渐浸入了他的人生观,以至于成为了他中晚年立身处事的重要准则。特别是在他晚年分司洛阳以后,自称“官秩三品分洛下,交游一半在僧中”。这个时候曾经的紫薇郎,如果再来看紫薇花,也许当是另外一种心境。 本期编辑小狐狸本期审核阿室 本期供图前3纵我不往中8葙葙芷再3重庆安礼后1智智 声明:本文欢迎阅读者在微博、沈阳最好的白癜风医院2019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iweihuaa.com/zwhsz/3639.html
- 上一篇文章: 紫薇花雨中,我在古森林博物园等你
- 下一篇文章: 行走花都六月紫薇正当时,紫薇,你在